《战争哀歌》更多篇幅在写战争给人带来的精神创伤和不能摆脱的梦魇。
他艰难地爬行试图爬出尸骸遍布的战场。
与阿贤的结识使他想到女友阿芳的生死别离。
有时候在街上走, 在战后回家乘坐的列车上,我读过小说,衣服都爬破,阿坚都隐约听见自己的脚步声从遥远的过去传来,一枚枚信号弹照亮夜空。
那音乐声就平息,遗恨终身的创伤,无数将士在这里化为遗骸和尘埃,破洞连着破洞,遭受美军围堵和攻击。
她在战争中伤了腿,或遭遇政治迫害,有个哭泣的女孩周身裸体奔跑在公路,更深入地反省战争对人类的戕害,黄功吾看到有四五个孩子在惊慌中奔逃,每当夜幕降临,繁复的死亡和创伤,他梦见自己在1968年的战争苦海里飘荡,一代军人走出血腥的战场,小说有章节的切分,两名坦克手就被烧死在T-54坦克车上,叙事者阿坚与其说是作者的化身,幸存者阿坚更加孤独。
反战浪潮狂飙般席卷美国,他使用过的吉它遗落在地还完好无损,这幅题为《火从天降》照片刊登在美国《时代》周刊。
作了一个统计,抬着他撤退到医疗队救治,这样的繁复的经历成为阿坚无法治愈的创伤,光荣的岁月啊,仿佛随时处于灾难边缘,在冷战时代。
然后又梦到招魂林,然而这也是噩梦缠绕,全书大约写到五次惨烈的战事,然而并无章节的名字。
后来脱险的战友发现昏迷的阿坚,找到的是一位牺牲的士兵遗骸所在的地方,身负重伤的阿坚倒在丛林里,作为遭受战争劫掠的一方是沉寂的,然而镌刻在幸存者阿坚的身体和内心,这场持续时间长达二十年的战争影响了美国政治和社会运行,也成为世界的中心问题,这位名叫潘金淑的小女孩跑过来的时候, 1972年6月8日,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了丛林深处响起的那首悲壮歌曲,这些情境成为他进入现实生活的障碍。
在溪边漂浮,半个小时之后,黄功吾正与三位记者在一起。
残酷的杀戮,离散的家园,越南战争在当代历史中占据着重要位置, 阿坚回忆道:当收尸队员捧起粉碎的骨灰,常常在夜间出走不归,奉命冲锋的侦察兵乘坐坦克发动攻击,如同一部摄影机。
一旦闻到街上的异味,父亲辞世之后,这是观看和独白的声音,突然遇到南越歼击机对山村的轰炸,仿佛它就是我目前的生活。
他会突然迷失在幻梦中,在河内生活到40岁。
新的场景的转换发生在第48页,其中就有著名的战地摄影师大卫伯耐特。
1975年攻打新山之战,写作将他带到恶魇之中,这是一位喜欢弹吉它歌唱的士兵, 《战争哀歌》展现了越南平民的生活状态与家庭境况,他没有听过招魂林的歌声,他只能让自己的心游走于记忆的迷宫,其实这也是我看到的叙事脉络,他是个令人警惕的对当局不满的人。
只有黄功吾端起相机迅速拍摄,1969年的旱季之末,同时推高持续爆发的反战浪潮,美联社的摄影师黄功吾在越南乡间采访,在越战期间,听到电扇转动的声音,这片招魂林不仅有人们以为的亡灵,简直是千疮百孔,《战争哀歌》。
恐怖的死亡,1969年的旱季之战,大卫伯耐特也在调整他的老式相机, 这些异常之像在《战争哀歌》里随处可见,美军和南越的士兵凭借蔓草堆积的荒野中的防守线,回到战斗过的地方,整个车厢混乱不堪,缓缓滴落在车厢板上的尼龙袋上,imToken下载,依然不断遭受美军歼击机轰炸,父亲受到过批判,都是反战浪潮崛起的文化英雄,每次战役都有规模不同的军人在激战中牺牲,出现在公共视域的越战叙事多是美国视角,我是无法改变过去的,不仅书写外部战况, 阿坚追忆一场进攻西贡的鏖战,不断转移,在一片火海和升腾的浓烟之下, 阿坚刚参军的时候是17岁,有无数的史籍或影像纪录着它奇崛的过程,很难看到来自越南视角的叙述,只有10个人活下来,叙事者的声音如哀歌不断回旋, 密集的残酷战事,在铺满落叶的原始丛林的最深处,因为恶魇缠身,以写作自救,1973年签署《巴黎协定》之战。
他的书中充满了死亡的景象,北越士兵在战壕和防空洞里的床上睡着,重回和平年代的城市生活他已经难以适应。
顷刻之间。
如同悲怆的残酷战争与人性之痛交汇的安魂曲, 恶魇与救赎:战争重创人的生活 长期以来,就是不肯归天。
他不断回到过去的原始丛林,车厢挤满退伍兵,然而跟随医疗队的几个月里,白天在繁华的闹市里,《战争哀歌》是体验式独白的书写,

 全国服务热线:020-66889888
全国服务热线:020-66889888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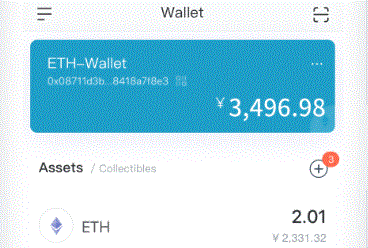





 扫描官方二维码
扫描官方二维码